《聊友》
我长长的伸了个懒腰,虽然仍是腰酸背痛,可心里说不出的轻松舒畅,两周来的疲劳一扫而空——个人主页的全新改版终于完成了。我挑了这个时间:凌晨三点,来上传我庞大的音乐和图片库。即便如此,恐怕没有几个钟头也传不完。成功的兴奋使我毫无困意,干脆去聊天室看看,不知这个点钟还有几只象我一样的夜游鬼泡在那里。
昵称:铁面判官 密码:******** 房间:幻想时空 GO!
凌晨的网络最是可爱,敲下回车,只用了几秒钟就登录进入了。公共聊天窗口里半天没有动静,看来大家都在捉对儿说悄悄话。看了看还剩几个人的在线名单,没有一个熟人。可反正是来了,索性随便找个人打个招呼,看有没有谁分得出空来理我。
“风里百合”?没劲,保不住是哪个变态大叔在那里搔首弄姿;“小猫喵喵”?幼稚,当阿姨的料;“金枪不倒”?嘿,真是无耻……正当我意兴阑珊的准备换个房间时,在线名单一闪,来了个新人,名字竟然叫——“阎王!!!”。粉红的颜色表明这是个女性网民。当然,至少也是她在注册的时候自称是女性。反正,网络虚拟的世界里,又有谁会在乎呢?
“喂!我是阎王!谁和我聊?”嘿嘿,一看就是个新手,一准儿要挨骂了……
“你去死!”果然,金枪不倒首先发难。好容易来了个恐龙独苗苗,可不能就这么让她被人骂跑!赶紧点下她的名字,选中“密谈”:
“你好,长官!”
“我不好。”
“不好?因为挨骂了吗?咱还是私聊,不要打扰别人好吧?”
“可以。不过我可不是因为挨骂才不好的,我一来就没好气儿!”
“那可怪了。为什么?”
“如果你兴冲冲的第一次来注册,却发现自己的名字早被别人抢注了,你还会好吗?”
“呵呵,可以理解。于是一气之下,小姑娘家的就叫阎王了?”
“你这个人理解力真差!阎王才是我的名字,那三个感叹号是不得不加上的!可气死我了!要不是有字数限制,真想注册叫‘我才是原装正版如假包换的阎王爷’!”
我开始觉得有一点儿有趣了:“这么说,您真是我的老板了,哈哈,好像这个月的薪水还没给我发吧?”
她倒一点儿也不含糊:“你这个判官是假冒伪劣的,我为什么要给你发薪水?再说,我们这里也没有钱这一说,大鬼小鬼们拼命工作挣的都是点数,挣够了九万点好换取‘转生证’,你要那东西有什么用?”
看来我今天是真遇上对手了。本判官向来以善于胡编乱侃闻名各大聊天室,今儿我倒要看看这个小妞能跟我扯到几时:“这倒怪了,刚才你叫唤‘气死了’,现在又说大鬼小鬼们‘拼命’工作,你们哪来的命,又怎么能死呢?”
她振振有词:“笨!没吃过鬼肉,总见过鬼跑吧?就算时运不济,连鬼跑都没见过,可总看过香港鬼片吧?连什么叫形神俱灭都不懂?你们死了变我们,我们再死了就什么都没了,就再也变不回你们了。所以我们这里对‘杀鬼犯’判得特别狠,受尽万般酷刑永世不得超生!”
我不由得头发根有点儿发麻——这小妞可有够恐怖的了。可总不能就这样低头服输,还得接茬儿找她毛病:“照你这么说,鬼是死一个少一个,那岂不是总有死光的时候?”
“说你笨你就笨,谁说鬼不可以娶妻生子?只不过和你们的原理不同而已。我们这里计划生育可搞得很好,基本维持了人鬼加起来的生命总数的恒定。”
“那倒挺美。可无论怎么说,我也没听谁念叨过阎王爷大人是个美眉啊!”
“你这人真是顽固不化!你们阳世早就废除君主制了,你当我们阴间还那么落后啊?我这个阎王,可是众鬼民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勇往直前推翻旧阎王的独裁统治后,由所有拥有政治权利的成年鬼民投票选举出来的!女的怎么啦?再看不起我们女鬼,我提前把你拘来!”
瞧这意思,她可是真有点儿不高兴了。得,让着点儿吧,管她是真是假,总是位女士嘛。
“好好好,算你厉害。阳世流行女强人,阴间当然也可以有女强鬼啦。就象武则天是吧?”
“嘿嘿,少来!我比她能干,可不象她那么淫乱!”
“越说你越没边儿了!别光是空口说白话!人家武大姐的政绩可是明摆着的,要是你真是阎王,你能给阴间来点儿什么重大改革吗?”
“当然,首先的一条,我认为就是应该加强和阳世的相互交流和理解。这样对双方都有好处。阳间的人总是怕死,我们这的鬼们又总是盼生,害得我们总不得不增加投胎指标,以至阳间人口爆炸,阴世冷落萧条。这样下去,早晚会有一天所有的生命都挤在阳间受苦,却忘了地下还有这片乐土。其实只要双方多了解沟通,这种矛盾很容易调和的。阴间并不可怕,也有爱和温暖。”
真是一派胡言,漏洞百出:“也许人世对阴间所知甚少,可阴间却应该是对阳世了如指掌的啊!鬼向生人畏死,自然有他们的道理吧?”
“你当然难以理解,事实上,阴阳转换的时候,一般情况下总会完全失去对另一个世界的记忆的。也就是说,没有几个鬼会记得他在阳间的经历。我们是真正的完全的另一个世界,没有谁能看得到那边,包括我。我们只能通过一种你们所无法理解的方式实现对生死的控制,仅此而已。不同的是,每个鬼都知道人世的存在,都在对那里向往;而人却总在恐惧肉体的无知无觉的死亡。”
我开始怀疑她是不是有什么毛病了。字打得这么快,怎么也是个五笔高手了,不会是神经有问题吧?难不成又是个“雨人”?偏是胡编滥造还编的条理清晰!
我硬着头皮又问了一句:“那你老人家会采取什么具体举措来改变这种现状呢?”
“你已经看到了,接入你们的互联网就是我的第一步。那样我们就可以用彼此都能够理解的方式交流。这可是我们研究院的鬼才们研究了好几年的成果啊!不过现在正在测试,只有我这里能连上去。”
“哈哈!那您用的是什么机器?可别告诉我是您老人家从中关村海龙大厦买配件自己攒的PIII!有没有摄像头?要不咱开个Netmeeting让我见识见识您的花容鬼貌?”我有点儿沉不住气了,话里话外不由得刻薄起来。
她却依旧不动声色:“那是你所不能理解的。人总喜欢由他们自己的经验去推测未知的东西。我们这里并不是个物质的世界,我也不需要什么电脑和调制解调器。我们的通讯设备,是以一种超乎你知识范围之外的方式存在和工作的。”
这家伙,太过分!竟然编起来没个头了。一气之下,我随手点开资源管理器,满硬盘乱翻一通,把丢了好久不用的几个黑客软件找了出来,准备给她点儿教训。可等我翻回聊天窗口,赫然发现在线名单里已经没了她的名字。
“算你跑得快!”我气哼哼的自言自语,“下回遇到,看我不炸你!”
转眼一周过去,每天编程序,写稿子,玩游戏,聊天。就在我几乎忘掉的时候,又一次在聊天室里看到了她的名字。奇怪的是,这时,我一点儿想黑她的念头都没有了。
“人生何处不相逢啊!假判官,咱们又见面了!”她这次主动打招呼了。
“错!你巨鬼一只,何来人生?”我还是余怒未消。
“呵呵,这次终于让你抓住把柄了。好,是我说错话了。不过真的很高兴又遇到你。”看来她今天心情不错。
“上次为什么不辞而别?”
“不是啊!我们这边在阴阳边界的数据转换上还有技术问题,联接很不稳定,特爱掉线!不过我的鬼才们刚取得了重大突破,不会再有类似的事发生了,所以我今天特别高兴!”
我可是真的有一点儿生气了。不管她是男是女,这样扯起来没边儿也够招人厌的了。拿出大叔的口吻训训她:“我说丫头,开玩笑总得有个限度,你一个小姑娘家,一天到晚总是鬼啊神啊的,变态啊?”
她半天没有反应。“大概气跑了吧,”我想。确实,我的口气未免重了一点。
“怎么,生气啦?”
“不。只是……,算了,当我没说。”
“好了,不开玩笑,你还没介绍过自己呢。哪里人?”
“就算是北京人好了。”
就算是——这叫什么话?
“还上学呢吧,哪所学校,大几了?”
“什么?”
“大学几年级!你真不明白还是装啊?”
“啊,那个,渤海大学,毕业两年了。”
天啊!和我同一所学校,还是同一级!
“学什么专业?”
“自控。”
我几乎乐得要蹦起来了,那肯定是我的同班同学!真象她所说,人生何处不相逢啊!
“那你叫什么名字?”打下这几个字时,手指都激动的有一点发抖了。
“为什么要告诉你?在网上随便问一个姑娘家的真名字不是有些失礼吗?”
看来不先招供她是不会相信我的了:“我是你同班同学!我就是黄晨啊!”
“我早知道你是黄晨。”
“怎么?你知道?怎么知道的?什么时候知道的?”
“我当然知道!我还知道你毕业不到半年就换了两次工作,最后还是炒了老板的鱿鱼;我还知道你现在自己独居靠个人主页的广告收入和稿费维生,活的还挺滋润;我还知道你的球踢得特棒,可毕业后就没再踢过;我还知道你喜欢音乐,吉他弹得远比你自己认为的更出色;我还知道前两天你们那里变天,你的腰伤发作的挺厉害,所以现在心情挺烦躁;我还知道电信多算了你的上网费,你正打算明天一早去找他们理论;我还知道,你去了也是白去,本来就是你误解了人家的收费标准;我还知道你不必再发愁硬盘不够用,因为你前天回复的一份有奖调查邮件将会替你得回那块30G的高速硬盘……我什么都知道,包括所有你不知道的。可你还是不相信我,对吗?”
盯着屏幕,我觉得一股凉气顺着脊梁骨冒了上来,嘴唇干得象要裂开,手抖得更厉害了。
“你怎么会知道?”
“简单得很,我并非你的什么同学,我早告诉了你我是谁。从一开始遇到你我就命令我这里的正宗判官把你的资料送了过来。我只不过是被你追着问的没办法了,才依照着你的学历回答你。”
一时间,我只觉得天旋地转,脑袋一晕,手指沉重的压到了键盘上:“法九阿飞低空拦截扩大反反复复方法分类……”一串毫无意义的字符发了过去。
“喂!喂!老兄!你没事吧!你又没做亏心事,干吗怕我叫门啊?”
看到这行字,我晃了晃脑袋,想想也没错,本“判官”自问从小到大始终是严于律己宽于待人,诚实热情乐于助人,大公无私舍己为人,……想来怎么也不应该会有什么恶报的。壮壮胆儿,稳定稳定情绪——
“那么说,以前你说的全都是真的了?”
“你是个挺可爱的人,我怎么会骗你?”
忽然,我想起一个重大问题,呼吸又急促了起来:“那么,你一定知道,我,我会在什么时候——死?”
长时间的沉默。
“喂!我说,不是又掉线了吧?你的鬼才们可信吗?”
“我想,我还是不告诉你吧。那对你对我都没有什么好处。清楚的知道自己的死期,无论对谁说都是件挺残酷的事;而我,也没有权力让你知道。”
“人的死期真是那样注定了就无可更改的吗?所谓阎王叫你三更死,谁敢拖延到五更?”
“倒也不是那么绝对。其实你们每分钟都有死亡的可能,只不过没到寿数总能躲过。我上任后,作了很大的改革,在我的权力范围内,尽可能放宽了死期的限制。现在基本是把死期定位在一年的区间,根据具体人的具体情况,在这段时间里随机的选一个比较适合他的死法。个人的努力也能对这段时间内的具体死期造成影响。”
“看来你是个挺有人情味儿的阎王啊!”
“呵呵,你不是说我巨鬼一只吗?哪来人情味儿啊?不过事实上,的确大多数人都通过种种努力拖长了他们的寿命。只要不超过最后期限,我就不会干涉。毕竟你们永远都是恐惧死亡的。”
我无话可说。不是吗?虽然总觉得活得挺累,可谁甘心失去生命呢?也许,人类怕的不是死,而是失去喜怒哀乐的所有感觉吧。不去想倒还好,真要假想一下自己冰冷的躯体,不再能有任何的动作和思想,那种发自人性最深处的恐惧,已不是我所能承受。
“算了,不要总去想这些。其实,也用不着去想。真到了必须面对那一天的时候,你会发现没什么可怕的。如果我告诉你死后很快就能找到个漂亮鬼媳妇,那就更不会怕了,对吧?你一直是个挺洒脱的人嘛,否则我也不会告诉你这些。”
“好吧。想不到阎王也会夸我一句,真不知道是个什么滋味。那现在,和阳间联上了网,你准备做什么?”
“其实,以你们的标准来说,我们这挺落后的,电信业还刚刚兴起。习惯了感应通信的大鬼小鬼们还不太认同这种看起来又麻烦又落后的通讯方式。现在我就像是个盗用了某个账号的拨号用户,只能实现最基本的网络功能。等我们这里的网络发达了,技术成熟了,建成类似你们大型服务器的通讯设备,找到与阳间的高速宽带的接入方法,恐怕至少也要几十年吧。我这条线路本来就是研究测试用的,我因为好奇,随便转转看看,和你聊上也完全是偶然。”
“偶然?连着两次也可以算是偶然的吗?”
“上次真的是偶然。我是因为你的名字才和你聊的。这次嘛,说实话,我是在等你。上次突然掉线,总觉得意犹未尽。忽然发现和阳间的人聊一聊原来是那么有意思。而我又不能随便见谁就说阴间的事。”
“你可真有闲心。看来阴间的头头比人世的容易做多了。”
“哪儿啊!都快累死我了!一天到晚处理不完的政务,还要当心政敌的中伤,承担鬼民的抱怨,忍受议会的牵制,一周下来也歇不了几个钟头!要不怎么隔这么久才来一次啊!再不找个人聊聊,怕我等不到任期满就要挺不住了。”
“呵呵,同情你!任期多长啊?”
“十年。好在还剩一年就要卸任了。”
“你这种阎王倒也少见,我似乎怎么也怕不起来你。”
“本来也没什么可怕嘛!好了,别总聊这些生生死死的啦,就当我是个普通聊友,随便和我聊聊吧,比如你们的生活,你的爱好……”
就这样,每周一次,固定的时间,固定的聊天室,我们总是要聊很久。后来,她干脆申请了一个“幽冥地府”的个人聊天室,设上密码拒绝其他人进入。这样一来,连扣帽子的网管也不用顾忌了,我们更是天上地下天南地北天涯海角的神侃。渐渐的,这每周一次的相会,已经象是饮食睡眠一样,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每到了那一天,我总会早早的联上网,首先打开我们聊天室的窗口,然后东游西逛,等待她的到来。她并不象我这样有空,从没有在这每周固定的一天以外的时间出现过,可也没有缺过一次,而且除了有限的几次,其余几乎都是一聊一个通宵。
半年多过去了,我甚至渐渐开始忘记了她的身份,开始怀疑当初不过是个巧合的玩笑,怀疑她不过是个异想天开喜欢恶作剧的普通女孩子。我追问她的名字,看来她好像也不喜欢我称她为阎王爷,挺痛快的就告诉了我。
“叫我灵吧。那真是我的名字。我不会骗你的。”
于是我再见到她就总是先叫上一句“灵灵”。她对我的擅自篡改也不怎么介意,后来干脆同流合污,也称我为“晨晨”了。我开始偶尔的给她传送一些文件,多半是我的弹唱录音或照片。她却一直不置可否,也没有任何的回应。然而,我们都再也无法掩饰某些东西,逃避某些话题。我们都是那么轻易的在对方的字里行间感受出对自己的深深依恋。我越来越渴望见到她——作为一个人世的普通女孩子。而她,却总是小心的回避着一切关于这方面的话题。
日子一周一周的过去。慢慢的,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的话少了下来,似乎有很重的心事。然后,某一天,当我进入我们的“幽冥地府”聊天室,赫然发现她竟然史无前例的在那里等着我。
“嘿,灵灵,新鲜啊!今儿怎么来这么早?”
“嗯。”
“什么时候来的?等了很久了吗?”
“嗯。”
“怎么了?哪儿不舒服吗?”
“没。”
“不要瞒着我!看过医生没有?”
“真的没事。”
“这两天热的反常,弄得我的头总是昏昏沉沉的。你是不是也一样啊?”
“嗯。”
“你们那里最高温度多少度?应该不会比我们这里还热吧?”
“唉……”
“怎么了,叹什么气?”
“你不用试探我了,我早就对你说过,我不会骗你的。不要再幻想忽然我说出自己在哪个城市,然后告诉你地址和电话号码,然后你就可以见到我——虽然我不知道多么希望能够那样。”
我觉得胸口象压了一块大石头,说不出的郁闷难受。
“我不会强求你不愿做的事的,你知道。可这几天不知道怎么了,我的情绪特别低落,真的是挺想和你面对面的聊一聊。虽然,我自己也提醒自己,那是不可能的……”
好长时间她那里没有动静。
“算了,是我不好,以后我不再提见面的事了好吧?”
“可该来的终究还是要来的……”她那里忽然没头没脑的冒出这么一句来。
我一阵狂喜:“你的意思是说……”
又是很长的沉默。我静静的等,生怕随手打错了什么话以至她改变主意。
“唉……,我感觉到你在期待和兴奋。可是你并没有真正理解我的话。你大概又忘记了,或者不愿再相信我的身份。现在我的心情不知道有多么多么的矛盾——从我自己来说,我不知道有多么多么想能见到你,可从你的角度,我却宁愿永远不会相见。”
我的心沉了下去,难道,真的是我在一厢情愿的幻想?难道,她真的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幽灵?难道,她说她的心情很矛盾,是我真的已经走近了人生的终点?难道……
“你不是说过阴间不必向往阳世,阳世也不必恐惧阴间吗?有什么话,大可以明明白白的告诉我。”
“可是对死的恐惧已经贯穿了整个人类的历史,又岂能是短期内可以消除的呢?洒脱如你者,如果我告诉你死期,恐怕也不一定能坦然面对吧?”
我静了下来,首次认真的思索这个问题。她久久的静默着,或者,在另外一个世界凝视着我的答案。我不知道她是否有身体,是否有形象,更不知道她的眼角是否有泪。
“不论我如何面对,终究是必须面对。忘了谁说过,哭也是个死,笑也是个死,为什么不笑着死呢?我相信自己能用平常的心态面对自己的死亡。若说有什么不甘心,那就是我真的不甘心象你过去说的那样,随着死亡而失去记忆中的一切——尤其是这最后一段。”
“那好吧,我告诉你。你的最后期限就是明天。也就是说,从去年的明天开始,你就随时有可能死去。我已经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东西,我已经无法再做得更多。”
无论我自以为如何,她的这句话还是把我送进了冰冷的深渊。我不愿相信。我才27岁,我有着远比常人健康强壮的身体;我始终谨守着我的人生原则,用满怀的热情和爱心对待这世上的一切;我热爱我的生命,始终对明天充满希望……不论从天理还是从人情,我都想不出有什么理由让我早殇。
她似乎知道我的感觉:“你不必抱怨,世上本没有善恶的标准和所谓的因果报应,那只不过是世人的杜撰。众多的生命,没有谁会去关注某个个体的行为。在每个生命开始的时候,都会得到一个随机数,那就是他的寿限——这才是真正的,绝对的公平。”
我深吸一口气:“是的,对我来说,如果要等到活得全无生趣只剩下对死亡的恐惧的那一天,实在还是明天死去的更好。尤其是,”我从里到外的兴奋起来,“我就快要见到你了,不是吗?”
“是的,你的一部分。”
忽然,我刚平静下来的心又抽紧了:“可是,我却不会记得你了,不会记得任何东西了,对吗?我会忘掉现在的一切,忘掉在这里发出和收到的每一个字,对吗?我会站在你面前,却是一片空白的站在你的面前,对吗?”
“一般情况下,是的。”
我欲哭无泪。
“不要难过。还记得吗——我说过那是在一般情况下。如果你真的愿意,你或者能保有记忆,可是那对你来说也许太残酷,而且没有任何人能帮你,包括我。”
“告诉我,灵灵,如何才能做到?我愿意付出一切,只要能记得你。”
“晨晨,我只能告诉你一句话——跨越生死的瞬间,如果想起我能给你足够的力量,使你不在沉睡中逃避所有的痛苦,你就可以留住全部的欢乐。”
盯着这句话,我若有所悟,陷入了沉思。世界仿佛就在这一刻停顿了下来……
也不知过了多久,眼前忽然一闪,将我从冥想中唤醒。
聊天文本区域里已经只剩下这一行字——“来吧,我等你。”
在线人员名单上已经只剩下我一个人——铁面判官。
外面,醒来的都市一片嘈杂。我却依旧静静的坐在电脑前。我已经写好了一份告别邮件,自动发送时间是今天午夜,收件人是我所有的朋友。
我也做好了一张启动软盘,插进了软驱。当那个邮件发完后,我的电脑就会重新启动,然后彻底格式化我的硬盘——我不想任何人看到我们的聊天记录。
我要死了。
可是我会怎么死呢?歹徒?车祸?还是地震?
“我就藏在家里,看她把我怎么办!”可偏头看了看厨房的煤气管道,我又胡思乱想起来——可不要因为我的最后期限,把其他人也牵扯进来吧。忽然,我起了一丝恶作剧的念头:已经不知道多少年没有玩儿过捉迷藏了,不是吗?
草草梳洗了一下,喝了杯奶(还好,没被呛死),拿出背包,随便塞进两罐可乐一个汉堡,背上我的吉他,走上了大街。
我只是不停的走,同时尽量的避开人群。我东张西望,到处寻找着能治我于死地的因素,同时想象着如何去避免。感觉里自己就象是走在莫斯科街头的007,危机四伏,步步陷阱,说不出的紧张刺激趣味盎然。后来,走到了香山。这时,我已经有点儿累了,我知道,这里有我想找的地方。
我在树丛中穿行,蜿蜒而上。也不知道走了多久多远,周围已再听不到人声看不到人迹。最后,我在一片绿草如茵的平缓山坡上坐了下来。抱起我的琴,才发现实在已经冷落了它太久。一根一根的,反反复复的把琴弦调准,轻轻一拨,叮叮咚咚。忽然间,只感到再无任何束缚的轻松。不再去想什么生与死,只剩下琴声和歌声。
天色渐渐的黑了下来,习习的微风把残留的暑气驱得一丝不剩。周围的树木花草一点点模糊,很快消失在浓黑的暮色里。城市的灯火却辉煌起来,映着满天的群星。喝了口可乐,我躺了下来,把琴横放在肚子上,随手弹拨。仰望着夜空,才发现,今天,这里,星光是如此的美丽,狂乱热情一如梵高的名画“星月夜”。嘿嘿,让我看看,哪颗是最亮的呢?
忽然,在我视线的正前方,一颗星在瞬间爆发出了眩目的光芒,而且越来越红,越来越亮,周围的一切都在它的面前黯淡了下去,同时似乎有隐隐的呼啸声从心底发出——那是一颗流星。我知道,在我看不到的它的另一面,一定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
“其实你们每分钟都有死亡的可能,只不过没到寿数总能躲过。”灵灵的话在我耳边响起。一丝微笑浮上了我的嘴角:她找到我了。那飞来的,是她送我的第一份礼物——美丽灿烂的死亡。
一切都不再存在,只剩下那种痛苦。身体似乎悬在虚空里,感觉自己被一分一寸的撕裂开,再被一丝一毫的揉碎。碎片一点点消失,痛楚却总是留了下来,不断的累积,无尽的膨胀,直到自己全部化作一团没有边际的痛苦,充满了整个宇宙,痛苦的中心包裹着我的灵魂。我已经不能思考任何东西,当周围似乎已化成有形之物的痛苦开始向我灵魂的中心挤压过来时,我忽然有了一种明悟——如果任由它们将我挤碎,我就不会再感觉到它们。
“不在沉睡中逃避所有的痛苦,你就可以留住全部的欢乐。”
来吧,全过来吧,我在心底狂喊:“灵灵,我不会沉睡!”
用残存的最后一丝灵明,我将自己的灵魂攥在一起,去顶受宇宙塌缩的重压。不知道过了多久,千分之一秒,还是亿万年,痛苦的宇宙和我的灵魂都凝成了虚空中的一个点,我再也无力去控制这介子里的须弥,爆碎开来,烟消云散。
我站在那里,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更不知道自己是何时来的。我感觉着周围的一切:感觉到了下面承托着我的能量场,知道了它应该叫做“地”;感觉到了上面覆盖着我的能量场,知道了它应该叫做“天”。感觉到了前面一团一团像我一样的东西,知道了他们应该叫做“同类”。我的兴趣转到了他们的身上。他们向我传递着大量的信息,我逐一的知道,那是“美丽”、“丑陋”、“强壮”、“瘦弱”、“喜爱”、“厌恶”……等到他们消失在我面前,我已经知道了:
我叫晨,是一个鬼魂;我刚结束了以“黄”为姓氏的上一次的人生旅程回来,接受完了例行的阴间迎接新鬼教程,学会了以另一种方式生存;我应该马上去向这里的最高长官——阎王报到;她将完成我旧生命的最后一道手续:在我的人生记录的最后一个栏目里填上“注销”然后归档;也将开始我新生命的第一道手续:发给我用来验证身份和记录点数的“身份卡”;接下来我将在众多的发展方向里任意的选择一个接受培训,以便有能力用工作换取点数,从而累积获得下一次人世旅程机会的资本。
我的感觉探了出去,很快的接通了阎王,并且迅速的向她的方向飘去。距离越近,却感觉头脑越混乱,刚学到的一切似乎总要破体飞去,同时发现在自己的某一部分竟然有一个不可感知的区域,而那里正越来越蠢蠢欲动。
终于面对阎王大人了。我感觉着她的美丽和温暖,也难以理解的感到了她的兴奋和不安。同时,那蠢蠢欲动的部分忽然狂烈的躁动起来,给我无比的惊疑和恐惧。
她身边众人中一个透出博学的书卷气的男子发话了:“下面来的,报上你的名字和准备注销的转生证编号。”
“你们早就知道,何苦再装模作样的问我一遍?”话出口,连我自己都大惊失色——这可不是我在迎新教程里学到的正确回答!天知道我怎么会迷迷糊糊的说出这些来!
所有人都惊呆了,只有阎王一下子绽放出欢笑的能量场。不知道她传出了什么信息,广阔的空间里忽然只剩下我们两个。她的思感深深的向我凝聚过来:“我的晨晨,你终于来了,你终于做到了。我说过,我等你!现在,醒过来吧!”
我那无法感知的区域忽然决口,被紧紧包在里面的全部记忆潮涌出来,瞬间填满了整个心灵:“灵灵!我来了!我终于见到你了!”
我向上飞去,去迎接那个飞向我的充盈着爱的喜悦的生命。
..20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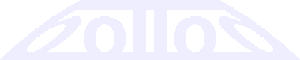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判官※
※判官※
 Post By:2008-07-01 23:43:04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8-07-01 23:43:04 [只看该作者]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判官※
※判官※
 Post By:2010-02-17 22:51:05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10-02-17 22:51:05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