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晨的琴,忽然断了一根弦。很莫名很离谱的一根弦。第五弦。
那段时间,他终于理清了自己的日常生活,可以有剩余的精力,安排几段闲暇的时间了。于是决定每天晚上九点半,完成了一天的任务后,关上门,倒上酒,开始练酒狂。
琴已经闲置了很久。揭掉蒙布,手指从弦上依次划过,发出微有些沉闷的声音。太久不碰,弦都有些滑松了,比正常的标准音高低了大约两三个半音。但好在整体滑松,各弦音程基本还准确,微调一下,还可以直接弹奏。况且很久以前,黄晨就更加偏爱这种更低沉的音色,本来就经常把琴调到比标准音高低两三个半音的。于是他便尝试弹奏了一下已经练过的曲子,基本还都能弹下来,手指的顽固记忆,远比他自己以为的更深刻。
黄晨便开始练习以前尝试弹过的,还记得谱子的酒狂的头一小段。
仅仅两三天以后,这难度并不大的一小段已经可以流畅弹下来了。该继续往下练新的了。而再往下,就要跟着教学视频往下学,必须再把琴调成跟视频里一样的标准音高了。
第一天。
黄晨坐下来,逐一旋紧琴轸,逐根调高琴弦。
调准后,试弹的时候,还没拨弄几下,忽然就发出了铮的一声。黄晨疑惑的抬起琴,检视雁足,检视轸子,没有任何地方有任何松动异常的迹象。再弹,其他弦一切正常,只有第五弦,又跳低回到了调弦之前的音高。
黄晨也说不上为什么,莫名的就感觉胸口郁结,心绪烦乱。但他也并没太在意,继续旋动轸子,重新调准了五弦,就开始继续向下练习酒狂的下一段。但是,不知怎么,每次拨响六弦的七徽九分,琴总会发出若有若无的砂音。
开始黄晨还以为是太久不弹琴体变形了。反复试验后,却发现,即便弹完就立即触断六弦七九这个音,砂音依旧若隐若现的持续。依次触断所有弦的共鸣音后,确定这个砂音来自于五弦的空弦。可无论如何单独拨响五弦空弦,却怎么也没有任何砂音。
黄晨又把岳山龙龈龙池凤沼所有地方检视了个遍,依旧找不到有任何毛病,就是只要拨响六弦七九,那个几乎细不可闻的砂音就阴魂不散的在耳廓里回荡。黄晨只好把这个恼人的砂音先放在一边,专心继续练习后面的曲子。
两个来钟头的练习,基本背熟了下一段的乐谱,也可以不用看视频断断续续的弹下来了。但每当弹响六弦七九,那个砂音总会像无形的刺一样,穿透耳鼓,钻进脑中。而且似乎越来越尖锐,越来越刺痛。
那天晚上,黄晨做了一个梦。
梦中,他缓步走在完全陌生的街头。两边是各种颜色缤纷造型诡异的建筑。前方是望不到尽头的地平线,正中是耀目的一个点。脑后,他不用回头,就清晰的感觉到,是逐渐向他压过来的一堵直抵天际的浓黑的墙。
随着每一步前行,两侧的一切都向他挤压过来。而他却感觉心底无限的平静。他甚至茫然的伸手去触摸挤压到他身边的建筑外墙,却并没能触到任何实质的东西,只是随着他的触摸,它们便分崩离析,旋转着消散开去。
渐渐的,他不由得一边前行,一边缓缓挥舞着双手,搅动着周围的漩涡。它们旋转,扭动,生长,渐渐与上面的天下面的地渗透融合。黄晨已分不清自己是在天地之间向前走,还是在虚空之中向前游。
他只感觉正前方那个点越来越亮越来越炫目。于是他向前伸出了手。
他那么清晰的看到,自己的手臂,化作一道逐渐延伸的虹彩,直射向前方。同时,耳畔传来无声的尖啸。他下意识的回过另一只手,仿佛一把抓住了身后的黑墙,拖着它,飞速投射向前,同时,似乎隐隐的听到了铮的一声。
虽然并没有方向,但突然袭来的坠落的感觉还是瞬间惊醒了他。
静静的躺在床上,黄晨努力回忆了很久很久。之前的一切无比清晰。但无论如何努力,总是想不起来自己最后飞向了哪里。
第二天。
坐在琴前,黄晨呆住了。其他六弦音准依旧。第五弦,再次跳回到了调弦之前那个低两三个半音的音高。
黄晨记起了昨夜惊醒之前听到的那铮的一声。轻轻晃了晃脑袋,默默伸出手,旋动轸子,再次把第五弦调准。继续今天的练习。
新学的谱子,记得无比清晰。不需要再看视频,只需要专心练手指。
两个来钟头后,弹得虽然依旧生涩,但已流畅了很多。按弦的左手拇指外侧隐隐生疼。但与被那个砂音变本加厉穿刺了两个钟头的大脑比起来,那点儿疼已经可以完全忽略不计了。而这种疼痛,甚至开始弥散开来,与胸口的郁结连接在了一起。
黄晨斜倚在床上,打开笔记本的播放器,单曲循环放上了酒狂的原曲,静静的抽完一支烟,一口喝干了杯中酒。
梦中。
黄晨一边缓步前行,一边举目四望。颜色缤纷形状诡异的建筑。面前的地平线炫目点,身后的浓黑墙。挤压,扰动,旋转。伸手。
当伸出的手开始加速延长射向前方时,黄晨想起了昨天,下意识的想要缩回来,但却发现,这个回缩的动作,千百倍的加速了投射。而身后,虽然这次他并没有反手去拉扯,那堵通天彻地的黑墙也千百倍的加速拍了过来,甚至拍出了那么清晰的铮的一声。
坠落,惊醒。
回忆,茫然。
第三天。
揭开蒙布,第五弦无力的斜搭着垂落,断了。于是黄晨知道,为什么昨夜那个铮的一声那么清晰。今天,二月十五。月圆。晴。
之后,每天,黄晨都想换上新弦继续练习。每天,却都会不知怎么就忘了。那一整套七根新弦,就那样一直放在琴桌上蒙布下。就这样,一晃,一个月。无梦的一个月。醉眼朦胧的一个月。
今天,三月十五,月圆不见,乌云密布,电闪雷鸣。出不了门,做不了事。闲。黄晨试图找个电影看看,可无论什么片子,不知怎么,看起来都那么索然无味。总有个什么听不清的声音,在召唤他。可是无论如何努力,依旧听不清。
傍晚,雨终于倾泻而下,敲打在窗上,发出的居然是金属般的铮铮声。
铮铮声。
铮。
断了整整一个月的五弦。
提前喝了一白天酒的黄晨,叹了口气,坐下来,用不可思议的速度,不可思议的容易的给琴换上了新弦。调好弦后,黄晨径直按住六弦七九,大指重托弹响。那个缥缈的砂音如约而至,穿透耳鼓钻进了脑海。只是,这次,毫无刺,毫无痛。沙沙掩盖笼罩之下,分明是南无阿弥陀佛揭谛揭谛波罗揭谛唵嘛呢叭咪吽E=mc2……
黄晨注视着五弦。不知是持续注视的失焦,还是共鸣产生的颤动,它变得越来越模糊,越来越宽泛,越来越透明。
黄晨点燃一支烟,倒满了酒杯。用手指沾了一滴酒,滴到烟颈上,深吸一口。甘醇和刺痛,通透和窒息。似乎,瞬间,烟就已经燃到了头,刺痛了他的手指。
黄晨知道,瞬间,其实并不是瞬间。瞬间,其实也就是瞬间。刺痛的,不是他的手指。是他那个在自我营造中膨胀到了临界点的气球。
于是爆开。宛如这个宇宙的初始。
什么是初始呢,什么是终结呢,什么是暴涨呢,什么是塌缩呢。什么是时,什么是空,什么是无可名状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维度。白驹过隙,芥子须弥,量子相干,时空谐振,黑洞,白洞,虫洞,各种洞…… 需要什么理由吗?存在什么理由吗?
我只知道,此时此地,三月十五,暴风骤雨,铮,召唤。
黄晨端起满满的酒杯,一饮而尽。
抬起左手,重重的按到六弦九徽。
按欲入木。
挥下右手,重重的勾响三弦空弦。
弹欲断弦。
挑六弦九,掐起,勾三,挑六弦七九……六弦七九……六弦七九……
旁观的,无关的,不相干的,五弦。
震荡,弥散。
忽然间,那个炫目的点,从震荡弥散的五弦某处爆开,周围的一切慢得似乎静止,快得似乎闪电一般,向黄晨挤压过来。
无声的尖啸。
狂暴的宁静。
酒。
狂。
虚。
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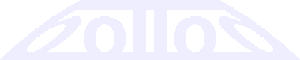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判官※
※判官※
 Post By:2017-04-18 19:31:28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17-04-18 19:31:28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