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她床边,我摸了摸她的额头,确实蛮烫手的。最奇怪的是,掀起一半的被罩下,露出的是她昨晚穿着的那件连衣裙。
她仰头看了看守在门口监视的宿管大妈,弱弱的说了一声:“在车站冻太久了,太累了。回来就睡了。真的。”
我倒是不必说什么。说什么都给了热心大妈更多想象的空间。况且,残忍点儿说吧,发烧而已。我发烧的时候,球队一声召唤,蹦起来就上球场的。虽然她并不是我,她跟我素不相识,但好歹大家都是人类吧。还穿着裙子倒省心了。我只需要搭把手,她就起来了。跟我走了。
又到了那个丁字路口,我问她:“医院?”
她摇了摇头。
那好吧。二舍。大妈,你就别在瞭望窗里恶狠狠的注视了吧。
现在,她躺在我的被窝里。其实也不算我的吧。开春以后,我就没盖过被子了。我只是在壁橱里找了一床闻起来不太刺鼻的被子拽出来给她盖上而已。至于脱掉到现在还潮乎乎的裙子和内衣这些事,轻车熟路波澜不惊了。我甚至懒得去想她究竟有多大必要让我动手。或许我没去学医真的是天大的错误。她只是个病人而已,虚弱,脆弱,需要照料。
“我做暑期家教勤工俭学,所以没回家。”
忽然间,我有点儿痛恨我自己了。为什么我就不能假装我什么都看不出什么都不知道,为什么我不能假装感动。为什么我甚至不能承认自己很猥琐的假装一段艳遇。
“我知道你没回家。就和我没回家一样,都有充足的理由。至于具体为什么,无关紧要。”
她定定的望着我,良久,说了一句:“你不相信家教。”
我也定定的望着她,良久,说了一句:“因为我做过。”
她忽然就笑了。很灿烂。她伸出了手,搂住我的脖子,把我拉过去,贴近我耳边说了一句:“是。咱们都做过。咱们都没回家。”
那个脸颊,真的很烫。
然后,她康复了。本来也不算病吧。
二舍没回家的学长学弟和老师们其实也并不是很少。但她说,一舍,只有她一个。毕竟这是个新学校。毕竟一舍是纯粹的女生宿舍。毕竟这还是很纯粹的年代,包括暗恋我的大学刚毕业的英语女老师,都住在二舍呢。
所以接下来的暑假,我再没机会见过一舍的宿管大妈。
其实,我自己的生活也并没什么太大的变化。依旧是每天睡醒,拎着塑料袋去海滩。回来,裸奔冷水浴,伏案学知识。
只不过,在二舍度过的时间,都多了一个她。
我们这一层,是大二大三的。只有我自己留校。一层二层是穿插的研究生和年轻教工宿舍,人很多,很热闹,但没有人会有兴趣往上层跑。三层是大一学弟,似乎也有几位在楼梯上见过,但毕竟是大一吧,什么都怕,不敢越雷池一步。楼上是大四的,虽然人比我们这层多些,但貌似他们假期留校,都有极端明确的目的,也没人会有闲空往下跑。所以,我的四层,成了真空。
于是,她后来甚至喜欢上了跟我一起裸奔到水房去冲冷水澡。或许是因为临近海边吧,水房的冷水,是地下水。真的很冷,很冷,很冷。
冷得让人欲罢不能。
尤其是,大多数的时候,我在海边的小海湾里泡了一整天,温吞吞的乌涂涂的海水,甚至当你爬上岸的时候都甩脱不掉那种暧昧的暖湿黏腻,你真的会无比渴望刀锋一样的冷。
在我的四楼转角水房里,龙头中喷出的是刺骨的冷冽,陪在我身边的是她。
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回想起来,我只在描述所谓战斗民族的网络段子里见过这样迷恋刺骨冰冷的女人。
当时,每当我洗完之后,如果赶上她也回来得早,赶上她也和我一起,她总会不停的往我身上喷冷水,一边叫一边笑,恳求我:”别跑别跑,再冲一会儿啊!“
我是燃烧性的体质。之后,迅速的,我就会回复正常体温。而我怀里瑟缩的她,就是我的冰激凌。她真的很喜欢这样,默默无声的吞噬掉我辐射出的所有热量。
开学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有一天,她忽然问我:“我知道你大三,叫东,明年毕业。你知道我几年级,叫啥吗。”
我真的愣了。我不是别的,我是真的愣了。我说:“其实我是大二的。第二次大二。我留级了。至于你,你是公交车站的那个偶遇的老师或是小师妹。你是叫裙子吗?”
她注视了我很久。笑的多少有些凄然吧,或许是真的,或许是我的错觉。她只是说:“谢谢你从没追问过我是谁。”
后来,开学了。她消失了。
说来也怪。这么小的学校,我从未再见过她。对她,我最后的记忆就是,开学前那一天,她紧紧的拥着我,对我说:“终于来了。好冷啊。好冷好冷啊。真的好冷啊,冷啊,啊。”
九月的第一天,是最冷最冷最冷的一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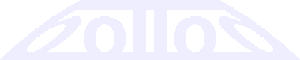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判官※
※判官※
 Post By:2017-04-30 2:24:07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17-04-30 2:24:07 [只看该作者]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判官※
※判官※
 Post By:2017-04-30 2:28:16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17-04-30 2:28:16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