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秋》
老人倚着靠垫,静静的侧躺在床上,背对着门,出神的望着窗外。天很蓝,团团絮絮的白云,有时候会有鸟在窗前飞过,洒下一路清脆的叫声。只有秋天才会有这样清爽透亮的天。门无声的开了,方推着小车,来给他送早餐。方看着老人安详的侧脸,看着洁白的房间,洁白的病床,看着床头小柜子上那只古铜色的大烟斗。方就那样静静的站着,不忍心扰乱那份宁静和恬适。
老人忽然笑了,回过头来看着方:“我的耳朵也许会老,我的鼻子却永远不会老。我能闻到牛奶和鸡蛋的香气。我还敢打赌,那是在你进来之前。”
老人的胃口很好。方喜欢看老人吃东西的样子,很香。方也喜欢推着老人在花园里漫步闲聊。那时候方就会听老人的话,叫他“老家伙”。老人说那是真正的褒义词,听起来比“首长”舒服多了。其实他真的不像九十的老人,眼睛依然那么清亮,思维依然那么敏锐,谈吐依然那么流畅。除了他艰难的从轮椅上站起倔强的非要走上几步的时候,你很容易忘记他的年龄。方有时就很迷惑,为什么偏偏是他们这些经历过最残酷最痛苦的事的人,却仿佛是活得最轻松呢?
“首长,打针。”那时方刚刚调来护理老人不久,老人染上了重感冒。老人一边拽纸擦着鼻子,一边笑眯眯的说:“谁让你来的?”方很迷惑,按照病例上的处方单子打针不过是很普通的程序啊。不过方忽然想起她推着药剂车出来的时候院长在门口看了她半天。老人饶有兴趣的看着她,继续说:“他们总是不放弃希望。好吧,就看看你如何说服我。”
干了这几年的护理,方早就知道,长期特护的人生活太单调,特别喜欢和人抬杠。“有病了就要用药啊,您这次病的很急,打针会好的快些。”
“那你说我得的什么病,要给我用什么药?”
方觉得很有趣:“您还在那擦鼻子呢,刚才试体温还在发烧,您当然得的是病毒性感冒,给您用的抗感消炎药啊。”
“不对啊孩子,我这叫染了风寒,是因为自己元气不足,经脉不畅,被寒气侵体了。”
方哭笑不得,老人竟然给自己讲起了中医理论。“可是不论怎样,病了就是病了,就要打针吃药的。”
老人板起了脸:“连病因都说错了还要用药,不是太不负责任了吗?小姑娘,我问你,你的国家弱小,帝国主义打进来了,你是要自己精厉图治发展国力把他打跑,还是把另一个帝国主义请来对付他呢?”
方哑口无言,政治课都上上了,再劝下去,“里通外国”的敌特嫌疑是免不了的。不过方觉得很委屈,打针治病而已,这老家伙哪还有这么多的牵扯呢?
老人的面孔忽然又解冻了,笑着说:“你是不是在心里骂我不通情理的老家伙啊?那你可就失算了。我最喜欢别人叫我老家伙。你要记住,今后别称呼我首长,好意思开口呢,就叫我老家伙;实在掰不开面儿,就叫我老伯伯好了。”
那次,老人终究还是没有打针。方也不再叫他首长。不过方还是不好意思把“老家伙”挂在嘴边,就一直称呼他老伯。
老人很快吃完了他的早餐。方推过了轮椅,这么好的天,老人照例是不会呆在病房里的。这一天的花园特别的美,很多花好像都赶在这一天开放了。
老人慢慢的在他的烟斗里塞上烟丝,用拇指压实,划了根火柴点燃,小心翼翼的把燃剩的火柴杆放在轮椅扶手上特制的烟缸里。老人从不在自然里留下一丁点儿垃圾,也极度的讨厌别人那样做。老人总说,他们这一代亏欠了这个地球太多,不能再继续作孽了。方不明白,老人说,她没经历过战火,不可能会明白。
老人很少跟方说起战争年代的事,仿佛那只是上映了太久的一部乏味的老片子,再不会有人去念起它关注它。不过方知道,每当老人静默沉思的时候,他都是在回忆那段岁月。现在老人就是这样了。在花丛中穿梭,老人却没有看花,只是凝视着烟斗中忽明忽暗的烟丝。走到花园一角的时候,老人忽然从沉思中醒来,说:“停一停。”方停了下来,发现老人在注视着草坪中一朵不知名的小黄花。它实在是太小了,虽然偌大的草坪里只有这一点黄色,可还是很容易被忽略掉。
老人忽然站起身走下了轮椅,前所未有的轻捷。方吃了一惊,却见老人蹲下身来,伸出手轻轻的抚摸着那小小的花瓣。而当他努力想站起来的时候,年龄却又一次战胜了他。
“我认识它,可我从来不知道它的名字。”坐在轮椅上,老人似乎有很多感慨。“一朵小野花罢了,郊外很多啊。”方不太明白老人对小黄花的在意。
“孩子,你有没有感到,生命是多么脆弱?几乎每时每刻,当我发现自己还活着的时候,都觉得那是个奇迹。”老人的目光注视着远方,穿越的不仅仅是距离,更是无尽的岁月。
空气中弥漫着硝烟,他射出了盒子炮里最后一发子弹后,愤然摔在地上。身子两边都是窜动的身影,他知道,那是用光了弹药的战士端着上好了刺刀的长枪。身边的通讯员已不知喊了多久,还在声嘶力竭的对着步话机喊:“总部!总部!请求火炮支援!请求火炮支援!”忽然仰天翻倒在地上,红红白白的,从后脑喇叭形的弹孔中汩汩涌出。他木然的看着,看着还在一下一下抽动的通讯员,看着身边掠过的一张张扭曲的面孔。步话机里传来总部的回应:“火炮就位!火炮就位!报告敌人方位,立即撤离!立即撤离!”
他知道,还剩两分钟。两分钟得不到回答,总部就会按照队伍已覆没,阵地已被攻陷处理,以阵地方位为打击目标进行轰炸。可是他这个指挥官如今如何能把这支陷入疯狂的队伍带离阵地呢?捡起通讯员身边的长枪,“啪”的一声扣上刺刀,他窜出了战壕向前冲去。
眼前似乎蒙上了一层淡红色的雾,晃动的身影都变得模糊了。传到耳朵中的各种声音却变得格外的清晰。金属撞击摩擦的声音,各种方言夹杂着“巴嘎”的叫骂声,没有语言区别的濒死的惨呼声,他忽然想起训练拼刺刀的时候齐刷刷的“杀”声,觉得很好笑,在这里竟然一声也听不到了。
鬼子依然是老习惯,只要敌人一端着刺刀冲下来就不再开枪。偌大的战场,已听不到什么枪响。想起队伍中流为笑谈的传说,遇到鬼子,上好刺刀再一枪一枪的打,鬼子临死还会大骂:“共军狡猾地!刺刀地干活,铁炮地给!”说共军不守武士道精神,我要跟你拼刺刀,你竟然开枪打我。
他盲目的向迎面遇到的人刺杀着,忽然发现自己竟然已冲过了短兵相接的阵线。回过头来,正看到两个同属他的队伍服色的人在他眼前拼杀。刺杀眼前一切活动的东西,这是肉搏战的规律。分辨敌我的空子,不知道会让身上多出多少个窟窿。任何一个从肉搏战战场上活下来的人都不会回忆起那战场。谁也不会知道自己结束了多少条生命,其中多少是敌人,多少是战友。
不过冲出战圈外围的他至少知道,现在端着刺刀向他冲过来的这个人是鬼子。周围没有其他的人,两个人的拼杀就少了些疯狂,有躲闪,也有挡架。不过狂热的杀戮情绪很快反扑了上来,两个人都已厌烦了叮叮当当,不约而同的挺起刺刀向前直刺。“咔嚓”一声,竟然是刺刀柄上的吞口挂在了一起,全身冲力的作用下,两人的胸口都重重的撞到了自己的枪柄上。从同归于尽的边缘走回,两人都呆在了那里,第一次彼此注视着对方的面孔。
就在这时,嘘嘘的尖啸声从空中传来,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密集,越来越响亮。战场上的声音忽然低了,只剩下几堆人还在疯狂的厮杀,更多的人开始丢下手中的一切东西不辨方向的拼命奔跑,还有一些人绝望的跪在地上抱头痛哭。所有的这些都没有任何的意义。他知道,很快,整个这片阵地上不要说活人,恐怕完整的尸首都不会再剩下。
第一枚炮弹在他不远处爆炸后,他就已看不到任何东西,听不到任何声音,做不了任何动作了。爆炸开始连成了一片,漫天是飞溅的砂石弹片和残肢断骨。忽然,他觉得右腿上一阵剧痛,同时整个身体被气浪抛了起来。身在半空的时候,他觉得手指触到了什么,就无意识的抓住。是一只手。这是他最后心中想到的。
方觉得快要窒息了。老人在这时候停了下来,仿佛如当年一般失去了全部知觉。方轻轻抚摸老人的右腿,原来这就是那片几乎覆盖了右大腿整个侧面的可怕伤痕的来源。沉吟了半晌,方终于忍不住问:“那只手……”
那只手,是的,那只手。老人醒了过来,当年的他也醒了过来。
醒来后,他第一眼就看到了那只手。那只手依然牢牢地攥在他的手中,另一端,上臂的骨头已断开,呲着惨白的茬口。还剩连皮带肉的一条,连在它的主人身上。就在这两只手的旁边,竟然,是暗绿的几片小叶,金黄的一朵小花。
他下意识的轻轻动了一下手,生怕一不小心就会让那脆弱的金黄夭折。或许是还会有痛苦的感觉吧,牵动了那只手的主人,在一声呻吟中也醒了过来。就是他,那个几乎与他同归于尽的鬼子。鬼子向他望来,显然也认出了他。从他残破的军装和腰间的空刀鞘上看出,他也是个军官。鬼子也看到了那朵小黄花,注视着它,眼光忽然黯淡了下来。
他向四周望去,斜斜的秃秃的山坡,遍布着弹坑和残骸。只有他们倒卧的小石崖下,有这几株小草,一枝野花。他再次望向鬼子,棱角分明的黄色的脸,黑黑的眼睛,黑黑的头发。他忽然发现自己的另一只手竟然还抓着那只上着刺刀的长枪。他默默地放开鬼子的手,卸下刺刀来,从军衣上割下长长的布条,扎住自己血肉模糊的大腿。犹豫了一下,他割断了鬼子上臂上残连的皮肉,又替他扎上了断臂。鬼子木然的任他摆布,仿佛那不是他自己的身体。
勉强站起身,他惊讶的发现自己身上竟然没有别的伤口。他不知该向鬼子说些什么,最后,指了指那朵小黄花,丢下手中的刺刀,艰难的向山坡上爬去。爬了一小段,身后忽然传来鬼子的一声闷哼。回头望去,鬼子用剩下的那只手把刺刀刺进了自己的腹部。
方发出了一声低低的惊呼。老人还在喃喃的说着:“我,和那朵小黄花,是仅余的幸存者。这就是战争。什么正邪,什么敌我,到了战场上,有意义的仅仅是生和死。”
暖暖的阳光照下来,方却觉得有些冷了。老人又燃着了一斗烟,望着满园的花,吞吐着浓浓的烟雾。“回去吧。”老人说。
回到病房,已经接近中午了。老人让方把院长叫来,说要提醒一下他答应过的事情。后来,老人拒绝吃午饭。再后来,老人睡了。
方问院长,他答应过老人什么。院长望向远方,眼光和老人一模一样:“我答应他,他濒危的时候,不要抢救他折腾他,让他平平静静的去。”
方独自来到花园中,久久的凝视着那朵小黄花。仅仅过了一中午,竟然已经有掉落的花瓣了。明天也许要下霜了吧,季节已经是晚秋。
..2002/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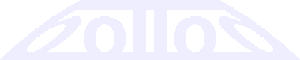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判官※
※判官※
 Post By:2008-07-02 0:05:43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8-07-02 0:05:43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