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突然传来的消息,用了我几乎一白天的时间去勉强化解。算起来,整整十年不曾需要如此之长的时间来专心的化解单一的情绪。无论有多少的记忆和恩恩怨怨,该去的人,总是要去的。我或许可以帮她缓释疼痛,却无法帮自己缓释茫然。毕竟我并非真的水族,此刻,是溺水的人终于爬上岸时的感觉。虚脱,放松,还或许,安全。
手指很痛,左手的拇指和无名指外缘都已经几乎起泡。它磨痛了我的手指,可它却是陪伴我游完从深水到岸边这段距离的。我总会尽量在独处的时候才弹起它。夫人说过,我虽无四妾却有三妻:她,电脑,琴。其实她不知道,我只有她一个妻,电脑和琴,都是我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延伸。
我知道,当我的一只手搭上岸边,犹疑着再过多久才要爬上去的时候,有个人拉了我一把。于是,我依然坚信没有任何人能拯救我,却开始有些相信总会有人能帮到我。尤其是,当你一直以来强硬的拒绝所有身边的帮助的时候,忽然帮到你的,总会是某种意义上的陌生人,因为你身边的人早已跟你一样相信你从不需要帮助。
情绪是一种很奇怪的东西。总会在你已经以为自己可以控制和把握的时候,跳出来给你一个下马威,提醒你,成长,成熟,是一个没有终结的过程。记忆也是个奇怪的东西,就好像格式化了十数次的硬盘,却不知什么时候跳出一个十数年前就删除的文件。然后你打开它,看到一字未改的语句,品味沧海桑田的心态。
从霍根海姆的喧闹瞬间回到完全静寂的午夜,我知道,那些已经过去了。当我已经可以静静的坐在这里用文字记录那些的时候,那些已经过去了。等到早上醒来,我会做个深呼吸,喝一杯清水后,带着一点点狂热和兴奋去到公司对付这两天攒下来的大堆工作。
生死之间,如此而已。无论那对于去了的人和去了的人所留下的人是否是解脱,依旧鲜活的永远只是此刻依旧鲜活的生命。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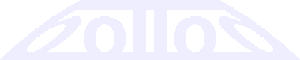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判官※
※判官※
 Post By:2004-07-26 2:35:05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4-07-26 2:35:05 [只看该作者]


